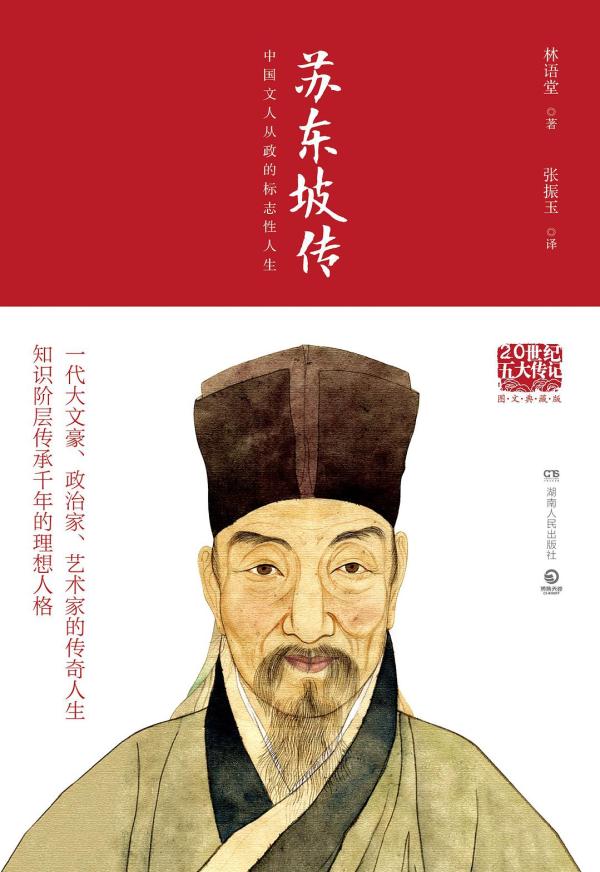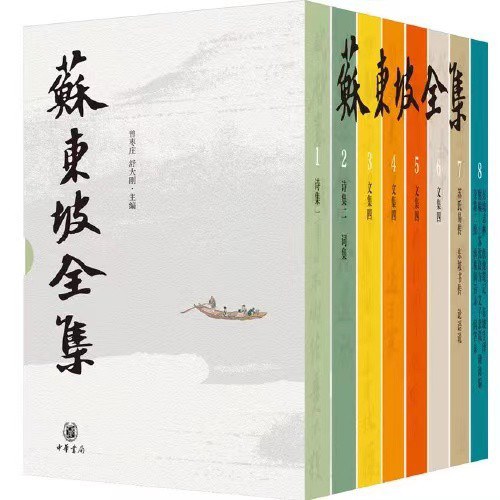作為千年一遇的曠世奇才�����,蘇軾在詩詞����、文賦��、書法���、繪畫、政治等各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���,而更難能可貴的是其人格的偉大���。九百多年來,蘇軾在政界��、學界和民間的深遠影響一直延續(xù)至今����。林語堂先生在其享譽海內外的《蘇東坡傳》中將其稱為“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�����、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�、一個百姓的朋友�、一個大文豪、大書法家�����、創(chuàng)新的畫家�、造酒試驗家、一個工程師��、一個憎恨清教徒主義的人��、一位瑜伽修行者����、佛教徒、巨儒政治家����、一個皇帝的秘書、酒仙、厚道的法官����、一位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、一個月夜徘徊者�����、一個詩人……”�,我們可親可愛可敬的東坡形象可謂躍然紙上。
蘇軾畫像
然而�,沒有“烏臺詩案”的重大轉折以及后續(xù)一系列的人生磨難,蘇軾的人生境界和文學藝術境界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���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���,蘇軾的人生是從黃州開始的(東坡這個流傳后世的名號也正是始于黃州時期)���,從這個著名的貶謫之地��,真正成熟的蘇軾開啟了堪稱輝煌的創(chuàng)作生涯(恰與其越來越艱難的命運形成鮮明對比)�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年(1101年)��,蘇軾在經過真州(今江蘇儀征)游覽金山龍游寺時,看到李公麟所畫蘇軾像���,回首命途多舛的一生�,一時感慨萬千����,寫下了著名的《自題金山畫像》: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����。問汝平生功業(yè),黃州惠州儋州�。苦澀蒼涼的詩句背后�����,卻透露出理解蘇軾人生和藝術的關鍵����,從黃州到惠州再到儋州,越貶越遠的東坡沒有被命運擊垮����,反而實現了政治人生和藝術人生的雙重升華���,最終成為了那個至今為人們口口相傳的男神蘇軾。
黃州:一蓑煙雨任平生
元豐二年(1079年)����,李定、舒亶���、王珪等朝中群小合力編織了臭名昭著的“烏臺詩案”(可謂中國古代政治生態(tài)的一個縮影)���。盡管有“不得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人”的祖宗家法,有病中曹后“不須大赦天下�,只放了蘇軾就夠了”的殷殷囑咐,有王安石��、張方平����、范鎮(zhèn)等一眾老臣的上書營救,蘇軾最終幸免于一死�,但仍因莫須有的詩罪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�����,其弟蘇轍、其書信往來之友王詵���、王鞏�����、張方平��、司馬光��、黃庭堅等20多人均受牽連被貶被罰�����,曾經風光無限的蘇軾可謂一落千丈��。然而�,正是“烏臺詩案”及黃州的苦難經歷��,讓這個天真的樂天派詩人真正走向成熟�����,走向更加曠達豪邁的人生�����。
黃州是一座偏僻蕭條的江邊小鎮(zhèn),任何人走到這里都不免會產生一種被遺忘���、被棄置的凄涼感����。初到黃州的那些天�����,作為犯官的蘇軾總是在白天睡上一整天����,到晚上才敢一個人悄悄地出門,他以這種晝伏夜出的生活來慢慢修復心靈的巨大創(chuàng)傷���。一天夜里����,他不知不覺間走到了遠離寓所定惠院的長江之畔�,所見的殘月、梳桐�����、冷夜�����、孤鴻����、沙洲等紛紛化作一個個詩的意象,尤其是那只孤獨而高傲的鴻雁�,在蘇軾心中引發(fā)深深的共鳴,它仿佛就是自己的化身:他的悲恨無人領會��,他的高致無人欣賞����,他的孤獨無人理解。于是�����,一首滿紙孤寂的《卜算子》從心頭奔涌而出:
缺月掛疏桐���,漏斷人初靜�。誰見幽人獨往來,縹緲孤鴻影����。
驚起卻回頭,有恨無人省���。揀盡寒枝不肯棲��,寂寞沙洲冷�����。
以創(chuàng)作為生命第一義的蘇軾��,如今卻不敢輕易寫詩作文�����,即便是寫給朋友的書信也往往再三叮囑“不須示人”��、“看訖���,火之”,唯恐“好事者巧以醞釀,便生出無窮事也”���。更令人可悲的是����,如雪花般紛紛寄出的信札��,幾乎都如泥牛入海一般�,從此杳無音信��。從前那些稱兄道弟的“朋友”��,如今已都作鳥獸散�,除了黃庭堅、秦觀等寥寥幾位摯友外�,誰愿意繼續(xù)和一個差點被砍頭的犯官為友呢!
然而���,正是這種前所未有的孤獨拯救了蘇軾����。自幼受到家庭佛教氛圍熏習的蘇軾��,開始真正親近佛教�,試著在靜觀默照中反思這場人生災禍����。他不怨天����,不尤人,而是從自身找原因�����。以佛學的觀念來看��,遭饞致毀是因自己屢犯“綺語戒”���,“口業(yè)”太盛����,而又固執(zhí)己見��。他痛切地認識到����,“才華外露”是自己做人的一大毛病。由此,他對自己做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?�。?ldquo;木有癭��,石有暈��,犀有通���,以取妍于人�,皆物之病也�。謫居無事����,默自觀省,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��,多其病者��。”(《答李端叔書》)這份沉痛懇切的反思�,去除的是根植于一己榮辱得失之上的“驕氣”,卻依然保留著忘軀為國的“銳氣”����,一種大格局、大氣象在這座千年小鎮(zhèn)上慢慢醞釀和生成。
林語堂《蘇東坡傳》
元豐五年(1082年)三月七日��,蘇軾在幾位熟識的朋友陪同下前往相田(打算買田置產)�。這日天朗氣清,大家一邊趕路����,一邊欣賞沿途的景致,沒想到倏忽之間風云突變����,一陣大雨即將傾盆而下,同行的朋友都覺得狼狽不堪����,只有蘇軾毫不介意。他仍舊腳穿草鞋�����,手持竹杖�����,和著雨打梳林的沙沙響聲���,一邊吟唱�,一邊行路。不一會兒���,雨過天晴���。這場倏然而至卻又倏然而去的大雨,讓蘇軾聯想到了自己所經歷的人生風雨�,他將之高度藝術性地化作了這首傳唱千古的不朽名作《定風波》:
莫聽穿林打葉聲,何妨吟嘯且徐行����。竹杖芒鞋輕勝馬,誰怕��?一蓑煙雨任平生�。
料峭春風吹酒醒��,微冷����,山頭斜照卻相迎?��;厥紫騺硎捝?��,歸去��,也無風雨也無晴�����。
竊以為�����,《定風波》一詞正是蘇軾在經歷大風大浪之后走向真正成熟的標志����。與古往今來許多大家一樣(正如被放逐于海利根施塔特的貝多芬)����,蘇軾成熟于一場災難之后,成熟于滅寂后的再生��,成熟于窮鄉(xiāng)僻壤�����,成熟于幾乎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刻。從此���,正是這份成熟讓蘇軾在詩詞���、文賦、書畫等各個領域大放異彩���。于是����,前后《赤壁賦》和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誕生了��,“天下第三行書”《黃州寒食帖》誕生了��,一個邁向人生和藝術至境的坡神誕生了����。
惠州:為誰合眼想平生
原以為黃州是蘇軾的人生谷底���,誰曾想到��,更多的災禍在等待著他���。元祐九年(1094年)四月�,哲宗下詔改年號為“紹圣”�����,意即繼承神宗朝的施政方針�。不久,呂大防�、范純仁罷職,章惇出任宰相大臣�。這位重回廟堂的變法派大臣,完全拋棄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體政策����,把打擊“元祐黨人”作為主要目標,盡情發(fā)泄多年來被排擠在外����、投閑置散的怨憤,蘇軾兄弟成為這場政治風暴的首要受害者�。仿效“烏臺詩案”的故技,朝中一幫小人網羅罪名�,橫加誣陷,蘇軾再度開啟貶謫生涯���。即使在千里迢迢奔赴貶所的路上���,小人們依然心有不甘��,屢進讒言�,朝廷竟五改謫命�����,最終將其貶為寧遠軍節(jié)度副使���,惠州安置�。經過近半年的艱險跋涉���,蘇軾最終抵達了當時的南蠻之地——惠州����。
兩年多的嶺南生涯在蘇軾波瀾壯闊的一生中時間并不長�,但卻有著極為特殊的意義,只因為一個人——朝云�。紹圣三年(1096年)七月���,蘇軾的愛妾�、一生的知己朝云病逝,年僅34歲�����。朝云的離去對于蘇軾無疑是一個極為沉痛的打擊��,這位“無可救藥的樂天派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凄楚之境���。自熙寧七年(1074年)蘇軾通判杭州時進入蘇家����,二十三年間朝云一直跟隨蘇軾輾轉南北��,無論升陟貶黜���,始終忠誠不二��。隨著蘇軾的貶謫�,曾經熱鬧的歌兒舞女們相繼散去�����,只有朝云隨他南遷,成為他悲慘的流放生涯中忠實的伴侶�����。即便到了瘴癘之地惠州�,朝云毅然無怨無悔,泰然自若�����,精打細算地操持著一家人的生活���,閑暇時便讀書念經���,習字臨帖,與蘇軾談禪論道����。
據說,朝云的生病和蘇軾填的一首詞有關�����。某日,貶居惠州的蘇軾和朝云閑坐����,正是秋涼時節(jié)�,蘇軾放下手中書卷��,見窗外落木蕭蕭�����,凄然有悲秋之感�,便請朝云演唱自己所填的《蝶戀花》(花褪殘紅青杏小)詞�����。朝云歌喉將轉����,淚滿衣襟,蘇軾驚而問之�。朝云說:“奴所不能歌者,唯‘枝上柳綿吹又少�,天涯何處無芳草’二句,為之流淚。”自此����,朝云常常若有所思,“日誦‘枝上柳綿’二句�����,為之流淚�。病極,尤不釋口�。”顯然,通曉禪理的朝云讀出了詞中的言外之意����,“枝上”一句,乃無常之象����,“天涯”一句,寫普遍之意��。兩句形象地道出了人生無常——恰似蘇軾一生的升降沉浮��,忽北忽南����。正所謂“霽月難逢�,彩云易散”�����,朝云不久后抱疾而終�,蘇軾也終身不再聽這首作品����。
難能可貴的是,朝云不只是同甘共苦的伴侶�����,更是精神相契的知己�����。想當年�,蘇軾故意捧著酒足飯飽的肚子問眾人:“你們可知道里面裝的是什么?”一位婢女說“都是文章”�����,另一位婢女說“都是學問”,直至朝云答道“一肚子不合時宜”��,蘇軾捧腹大笑���,贊道:“知我者���,唯有朝云也。”如今��,形單影只的東坡先生只能在惠州西湖邊徘徊游蕩����,夕陽斜射的樹林間寒鴉盤旋,寺院的晚鐘與佛塔的鈴語����、瑟瑟的松吟相互應和,構成了如此凄迷的意境���。這里的一山一水�,一草一木��,無不令人想起朝云����,于是便有了《西江月·梅花》:
玉骨那愁瘴霧��,冰姿自有仙風���。海仙時遣探芳叢。倒掛綠毛么鳳�。
素面翻嫌粉涴,洗妝不褪唇紅�。高情已逐曉云空。不與梨花同夢�。
這首詠梅詞�,寫嶺外梅花玉骨冰姿,素面唇紅��。然而�,曉云已散(喻朝云病故),蘇軾不能像王昌齡夢見梨花云(雪景)那樣做同一類的夢了����。句句詠梅,卻又字字懷人����,于朦朧中寓深情���,于哀婉處見幽致。其間之一往情深���,不讓東坡千古悼亡詞《江城子》(十年生死兩茫茫)�����,千載之下�����,令人動容��。
張充和《仕女圖》
朝云死后���,蘇軾遵照其遺言,將她安葬在豐湖岸邊棲禪院東南山坡上的松樹林間�����。據蘇軾所撰的碑銘記載:“(朝云)且死����,誦《金剛經》四句偈以絕�����。”四句偈便是著名的“一切有為法��,如夢幻泡影���,如露亦如電,應作如是觀”���,因有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之語��,又名“六如偈”�����。后來,寺院僧人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��,取名“六如亭”�,亭柱上鐫有蘇軾親自撰寫的一副楹聯:“不合時宜,惟有朝云能識我��;獨彈古調�,每逢暮雨倍思卿���。”縱觀蘇軾曲折的一生,幸有幾位于他有特殊意義的至親女性:他的母親程氏�,他的兩位夫人王弗、王閏之�����,朝云是身份更低但更為重要的一位�。正所謂詩云:“四弦拔盡情難盡,意足無聲勝有聲�����。今古悲歡終了了��,為誰合眼想平生��。”(張充和《仕女圖》題詩)
儋州:茲游奇絕冠平生
本想在惠州了此殘生的蘇軾萬萬沒想到����,另一個更加悲慘的厄運即將降臨到自己身上。紹圣四年(1097年)又一個不祥的四月����,惠州知州方子容懷著沉重的心情專程前來����,并正式傳達了朝廷的告命:責授瓊州別駕�����,昌化軍安置��。據說���,朝中群小看了蘇軾在惠州寫的詩句�����,諸如“嶺南萬戶皆春色�����,會有幽人客寓公”、“日啖荔枝三百顆�����,不辭長作嶺南人”等等,認為他在惠州還是生活的太舒服���,應該貶到更遠更蠻荒的地方�,于是直接發(fā)配天涯海角����。要知道,在北宋一代���,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輕一等的處罰���。
踏上海南島,對長居大陸的蘇軾而言�����,已沒有過去那種“仿佛曾游”的神秘感覺�����。登高北望��,視野所及��,只有一片浩淼的海水,四顧茫然�����,一種異國他鄉(xiāng)�、永無歸路的凄涼感襲上心頭。海島的生活相比黃州��、惠州��,可以說才是真正的艱難����。這里地熱海寒,林木陰翳�����,燥濕難耐��,毒物遍布���,被中原人士視為十去九不還的鬼門關���。初來乍到的蘇軾面對食無肉、病無藥����、居無室、出無友�、冬無炭、夏無泉���,更無書籍和筆墨紙張的艱難窘境����,加之語言不通��,簡直是度日如年�。但蘇軾之所以是蘇軾,就在于無論他走到哪里�,都有非凡的自信和本領,生生將“地獄”變?yōu)?ldquo;天堂”��。
《蘇東坡全集》
隨著蘇軾繼續(xù)發(fā)揮他“上可陪玉皇大帝����,下可陪卑田院乞兒”的隨和寬容的人格魅力,他逐漸適應了黎民的風俗���,也贏得了當地各族人民的愛戴和關懷��。爾后���,他在這里辦學堂��,介學風��,育學人����,以致許多人竟不遠千里���,追至儋州拜于蘇門�����。北宋一百多年時間里����,海南從無人進士及第�����。但蘇軾北歸后不久,儋州姜唐佐就舉鄉(xiāng)貢��。為此���,蘇軾曾題詩:“滄海何曾斷地脈,白袍端合破天荒���。”至今����,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儋州文化的播種人和開拓者��,對他懷有深深的敬意�。
同時,這種返璞歸真的散淡生活讓蘇軾邁向人生的更高境界�,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陶淵明。對比其嶺海前后的詩風����,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由超邁豪雄向淡雅高遠的轉變,正所謂“絢爛至極歸于平淡”��,藝術史所津津樂道的晚期風格(Late Style)在蘇軾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���,其最顯著的例證便是他一百多首“和陶詩”��。在惠州�����、儋州兩地���,蘇軾幾乎和遍了所有陶詩����。最后����,他得出了這個著名的結論:
吾與詩人無所甚好,獨好淵明之詩����。淵明作詩不多,然其詩質而實綺�����,癯而實腴,自曹�、劉、鮑��、謝�、李、杜諸人����,皆莫及也�。(《與蘇轍書》)
在此,陶淵明成了蘇軾晚年打量自己的一面鏡子���,他承認自己的詩“不甚愧淵明”�,但在人生境界上則“深愧淵明”��,并表示“欲以晚節(jié)師范其萬一也”���。事實上�����,蘇軾和陶淵明兩位異代大詩人可謂是相互成全���,在陶淵明詩文復興的漫長之路上�,蘇軾晚年的極力推崇可謂居功至偉���,而在蘇軾晚年遭遇一貶再貶的人生困境中���,陶詩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慰藉和美學滋養(yǎng),對蘇詩晚期風格的形成影響巨甚��。
風燭殘年之際�����,蘇軾迎來了頗具反諷意味的命運反轉�。元符三年(1100年)正月初九,哲宗崩逝�,徽宗繼位,政局大變��。神宗妻向氏以皇太后垂簾聽政�����,形勢向著有利于元祐臣僚的方向迅速發(fā)展��。二月,便大赦天下�����。待到六月�����,蘇軾終于要離開謫居三年之久的儋州�,當地的土著朋友紛紛攜酒帶菜前來餞行,執(zhí)手泣涕�。在渡海的當晚,蘇軾一夜無眠�,看著天容海色��,他聯想起自己多舛的一生�����,盡管謗誨交加��,但高風亮節(jié)終將長留天地�����,一時間詩思泉涌,不禁脫口吟道:
參橫斗轉欲三更���,苦雨終風也解晴�����。
云散月明誰點綴��?天容海色本澄清����。
空余魯叟乘桴意����,粗識軒轅奏樂聲。
九死南荒吾不恨�����,茲游奇絕冠平生����。
此際,他終于領悟了莊子齊得失���、等榮辱的哲理���,看透翻云覆雨的政壇變幻�����,就像孔子所感嘆的:“道不行�,乘桴浮于海����。”盡管他已下決心歸隱江湖,但隨著時間的推移��,蘇軾將出將入相的消息已傳遍全國����。這時�����,章惇之子章援驚恐焦慮萬分���,因為他父親當年正是迫害蘇軾的關鍵人物之一���。他只能厚著臉皮���,專門給蘇軾去信替父親求情(其時章惇已被貶雷州),擔心蘇軾回到朝廷后�����,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��。其實���,這種擔心完全是多余的��。邁過耳順之年的坡翁早已跳出了是非恩怨的小圈子����,而以了悟人生的智者眼光與悲天憫人的仁者胸懷俯視一切人事��。
收到章援來信時���,蘇軾已身染重病��,卻仍強支病體回書作答���。他十分誠懇地寫道:“某與丞相定交四十余年��,雖中間出處稍異����,交情固無增損也�����。聞其高年寄居海隅����,此懷可知。但以往更說何益�,唯論其未然者而已。”不僅如此�����,蘇軾還將自作的《續(xù)養(yǎng)生論》一篇及行之有效的養(yǎng)生藥方隨信寄贈����,希望他能借此頤養(yǎng)天年�,熬過這人生一大劫難�。就這樣�,蘇軾一筆勾銷了往日的恩怨,其胸懷是何等開闊�,境界是何等高遠!據史書記載���,章家一直珍藏著這封感人至深的回信���,幾十年之后,還有人從章惇的孫子章洽那里看到�����。
建中靖國元年(1101年)七月二十八日�,蘇軾在北歸途中病逝于常州,享年65歲���。一時間���,舉國震悼,山河同悲����。蘇軾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��,這位中國文化史上的罕見全才給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遺產����,包括2700多首詩���、300多首詞��、4200多篇散文�,以及無數書畫藝術杰作�����,人們將蘇軾所創(chuàng)造的文化世界尊為“蘇海”���。更重要的是�����,蘇軾巨大的人格魅力傾倒和影響了無數中國人�����,人們不僅欣羨他在事功世界中剛直不阿的風節(jié)���、民胞物與的赤子之心,更景仰他心靈世界中灑脫飄逸的氣度���、笑看風云的超邁����。這位將現實性與超越性完美交融的人生典范����,永遠令人追慕,惹人懷想����,予人啟迪。